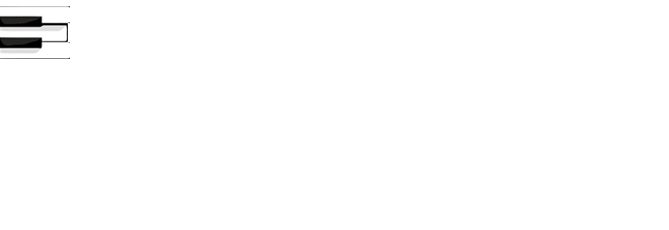咨询预约: 18021324435 张老师
Q Q: 934682552
客服电话: 0514-87903667
地 址: 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中路与文昌中路交界东宇大厦
扬州成人钢琴培训-那些著名的临终时刻(扬州21piano专业成人钢琴声乐培训)
www.21pianoedu.com
扬州成人钢琴培训-那些著名的临终时刻(扬州21piano专业成人钢琴声乐培训)
音乐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迷恋临终一刻。一位伟大作曲家的临终痛苦代表了救世主的受难,是一种崇拜的仪式。我们充满敬畏地观看,然后期待救赎。
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据说他是为自己而作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据说他是为自己而作
我们爱的不是死掉的作曲家,而是快死的。音乐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迷恋临终一刻。没有人记下莎士比亚的临终遗言,没有人为死在床上的达·芬奇画像,但每一位略有名气的作曲家,都有或粉饰或伪造的临终记录,这种病态的热情几近恋尸成癖。
首先遭殃的是偶像级人物莫扎特,据他的妻子说,他临终前一边挣扎着写一首安魂曲,一边说此曲“是为了自己而作”。后来者还有马勒,据他那满口谎话的太太阿尔玛说,他的临终遗言是“莫扎特”,虽然马勒还没死阿尔玛就已经离开了房间。
有一打书籍和上百篇博士论文探讨了柴科夫斯基之死,起先大家以为是霍乱,后来大家认为他是自杀,因为害怕同性恋丑闻公之于众。尽管学者们爱拿“悲怆”交响曲当证据,却没有什么研究真正挖掘出这部作品情绪或意义上的新意。
窥私癖们入侵了苦行僧安东·冯·韦伯恩(Anton von Webern)之死,1945年9月,他在走私犯女婿家中被一位美国大兵射杀;还有绝望的年轻加拿大人克劳德·维维尔(Claude Vivier),在巴黎街头被意外捅死。
韦伯恩之死被彼得·格林纳威拍成了电影,维维尔之死被编成了一出演员表演的电视纪录片。衍生纪念品随处可见。你可以买到贝多芬的死人面部模型,甚至可以在ebay上买到所谓的他的头发。苏富比拍卖行时不时会出现已故作曲家的眼镜或是香烟盒。
作曲家本人则沉溺于互写死亡告示。1911年5月,阿诺德·勋伯格从马勒的葬礼上回来后,就写了一首短小的钢琴作品,然后坐定,画下了陵墓场景。拉威尔用《库普兰之墓》寄托哀思。1977年,阿沃·帕特(Arvo Part)在纪念本杰明·布里顿的缓慢圣咏中开始了苏联晚期作曲家的政治反抗。
死亡热也不忘染指图书。《肖邦的葬礼》光看书名就知道它独特的卖点,传记作者本妮塔·埃斯勒(Benita Eisler)将这位波兰钢琴家描写为用艺术预示自己死亡的多病典型。书中生动地记述了肖邦停止呼吸的那一刻,两个狗仔记者冲进房间搬弄家具,为了拍摄尸体能有更好的光线。比起那些靠肖邦的后代生活的腐食乌鸦们,他们似乎也并没有坏到哪里去。
并无迹象显示肖邦之死有何特殊之处,但埃斯勒将他视为浪漫之死的典范,他的《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》几乎在所有国葬上都能听到。 另一本书《弗朗茨·李斯特之死》中的墓地闹剧更是骇人。曾经写过三卷本《李斯特传》的大权威艾伦·沃克(Alan Walker)找到并出版了丽娜·施默豪森(Lina Schmalhausen)的日记,描写了李斯特的最后日子。丽娜是那些吻过李斯特法衣末端的年轻傻女人中的一员,她曾被控小偷小摸,但虚弱的老大师几乎无法站立,总是让她在旅途中陪伴左右。人们常常看到他俩手拉着手。
1886年7月,李斯特让丽娜来拜罗伊特看他,他的女婿瓦格纳三年前去世,女儿科西玛正在安排第一次音乐节。丽娜这两周的日记如此生动而详细,以至于科西玛和她的王朝将之严防死守了一个世纪。沃克教授以权威身份宣布这日记绝对可信。
丽娜痛斥了拜罗伊特的江湖医生将肺炎诊断为普通感冒,瓦格纳的孩子们也很少去探望将死的外祖父。“别让我死在这儿,”李斯特乞求道。科西玛和父亲的关系极为冷淡,在李斯特病情恶化后,她禁止丽娜来家探视,并保证自己会守夜。丽娜躲在灌木丛里偷看。科西玛走时锁上了房门,将父亲变成囚犯。她去剧院时,丽娜从仆人通道偷偷进了屋。“别离开我,”李斯特哀求道,“她不会那么快回来的。”之后,丽娜躲在窗外看见科西玛离开时都没有亲吻父亲的额头。凌晨两点,李斯特在抽搐中摔下了床,仆人叫醒了科西玛。
她叫了医生,一个半小时后才到。李斯特那时已经昏迷。第二天才来了一位专家。丽娜恨恨地写道:这是科西玛唯一一天一直陪在老父床边。丽娜躲在灌木丛里一直偷看到傍晚。当晚她被叫醒告知李斯特去世的消息。她选了一束勿忘我,在科西玛同意后放在大师两手之间。她的花束被摄入相片中而不朽。
丽娜还说,瓦格纳的孩子们在祷告时无一落泪。李斯特的尸体旁围着苍蝇,涂油也搞得一团糟。科西玛不得不和一个仆人一起将尸体抬进棺材,然后再搬到街对面自己的房子里去。她还放开了狗链,让狗四处乱跑吓走不速之客。李斯特的钢琴学生们痛饮一番,葬礼毫无庄重可言。对于整个拜罗伊特来说,不过是瓦格纳的岳父去世了。“悲惨的结局。”丽娜这样写道。
丽娜的描述如此动人,使得这出未经粉饰的人性戏剧成为音乐知觉中永恒的回音。我们为何如此想知道临终情形,是音乐学这门浅薄的科学所无法参透的奥秘。我怀疑根源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批评的。这与古典音乐取代已被抛弃的基督教信仰,在世俗年代中满足听众的功能有关。一位伟大作曲家的临终痛苦代表了救世主的受难,是一种崇拜的仪式。我们充满敬畏地观看,然后期待救赎。
音乐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迷恋临终一刻。一位伟大作曲家的临终痛苦代表了救世主的受难,是一种崇拜的仪式。我们充满敬畏地观看,然后期待救赎。
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据说他是为自己而作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据说他是为自己而作

我们爱的不是死掉的作曲家,而是快死的。音乐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迷恋临终一刻。没有人记下莎士比亚的临终遗言,没有人为死在床上的达·芬奇画像,但每一位略有名气的作曲家,都有或粉饰或伪造的临终记录,这种病态的热情几近恋尸成癖。
首先遭殃的是偶像级人物莫扎特,据他的妻子说,他临终前一边挣扎着写一首安魂曲,一边说此曲“是为了自己而作”。后来者还有马勒,据他那满口谎话的太太阿尔玛说,他的临终遗言是“莫扎特”,虽然马勒还没死阿尔玛就已经离开了房间。
有一打书籍和上百篇博士论文探讨了柴科夫斯基之死,起先大家以为是霍乱,后来大家认为他是自杀,因为害怕同性恋丑闻公之于众。尽管学者们爱拿“悲怆”交响曲当证据,却没有什么研究真正挖掘出这部作品情绪或意义上的新意。
窥私癖们入侵了苦行僧安东·冯·韦伯恩(Anton von Webern)之死,1945年9月,他在走私犯女婿家中被一位美国大兵射杀;还有绝望的年轻加拿大人克劳德·维维尔(Claude Vivier),在巴黎街头被意外捅死。
韦伯恩之死被彼得·格林纳威拍成了电影,维维尔之死被编成了一出演员表演的电视纪录片。衍生纪念品随处可见。你可以买到贝多芬的死人面部模型,甚至可以在ebay上买到所谓的他的头发。苏富比拍卖行时不时会出现已故作曲家的眼镜或是香烟盒。
作曲家本人则沉溺于互写死亡告示。1911年5月,阿诺德·勋伯格从马勒的葬礼上回来后,就写了一首短小的钢琴作品,然后坐定,画下了陵墓场景。拉威尔用《库普兰之墓》寄托哀思。1977年,阿沃·帕特(Arvo Part)在纪念本杰明·布里顿的缓慢圣咏中开始了苏联晚期作曲家的政治反抗。
死亡热也不忘染指图书。《肖邦的葬礼》光看书名就知道它独特的卖点,传记作者本妮塔·埃斯勒(Benita Eisler)将这位波兰钢琴家描写为用艺术预示自己死亡的多病典型。书中生动地记述了肖邦停止呼吸的那一刻,两个狗仔记者冲进房间搬弄家具,为了拍摄尸体能有更好的光线。比起那些靠肖邦的后代生活的腐食乌鸦们,他们似乎也并没有坏到哪里去。
并无迹象显示肖邦之死有何特殊之处,但埃斯勒将他视为浪漫之死的典范,他的《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》几乎在所有国葬上都能听到。 另一本书《弗朗茨·李斯特之死》中的墓地闹剧更是骇人。曾经写过三卷本《李斯特传》的大权威艾伦·沃克(Alan Walker)找到并出版了丽娜·施默豪森(Lina Schmalhausen)的日记,描写了李斯特的最后日子。丽娜是那些吻过李斯特法衣末端的年轻傻女人中的一员,她曾被控小偷小摸,但虚弱的老大师几乎无法站立,总是让她在旅途中陪伴左右。人们常常看到他俩手拉着手。
1886年7月,李斯特让丽娜来拜罗伊特看他,他的女婿瓦格纳三年前去世,女儿科西玛正在安排第一次音乐节。丽娜这两周的日记如此生动而详细,以至于科西玛和她的王朝将之严防死守了一个世纪。沃克教授以权威身份宣布这日记绝对可信。
丽娜痛斥了拜罗伊特的江湖医生将肺炎诊断为普通感冒,瓦格纳的孩子们也很少去探望将死的外祖父。“别让我死在这儿,”李斯特乞求道。科西玛和父亲的关系极为冷淡,在李斯特病情恶化后,她禁止丽娜来家探视,并保证自己会守夜。丽娜躲在灌木丛里偷看。科西玛走时锁上了房门,将父亲变成囚犯。她去剧院时,丽娜从仆人通道偷偷进了屋。“别离开我,”李斯特哀求道,“她不会那么快回来的。”之后,丽娜躲在窗外看见科西玛离开时都没有亲吻父亲的额头。凌晨两点,李斯特在抽搐中摔下了床,仆人叫醒了科西玛。
她叫了医生,一个半小时后才到。李斯特那时已经昏迷。第二天才来了一位专家。丽娜恨恨地写道:这是科西玛唯一一天一直陪在老父床边。丽娜躲在灌木丛里一直偷看到傍晚。当晚她被叫醒告知李斯特去世的消息。她选了一束勿忘我,在科西玛同意后放在大师两手之间。她的花束被摄入相片中而不朽。
丽娜还说,瓦格纳的孩子们在祷告时无一落泪。李斯特的尸体旁围着苍蝇,涂油也搞得一团糟。科西玛不得不和一个仆人一起将尸体抬进棺材,然后再搬到街对面自己的房子里去。她还放开了狗链,让狗四处乱跑吓走不速之客。李斯特的钢琴学生们痛饮一番,葬礼毫无庄重可言。对于整个拜罗伊特来说,不过是瓦格纳的岳父去世了。“悲惨的结局。”丽娜这样写道。
丽娜的描述如此动人,使得这出未经粉饰的人性戏剧成为音乐知觉中永恒的回音。我们为何如此想知道临终情形,是音乐学这门浅薄的科学所无法参透的奥秘。我怀疑根源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批评的。这与古典音乐取代已被抛弃的基督教信仰,在世俗年代中满足听众的功能有关。一位伟大作曲家的临终痛苦代表了救世主的受难,是一种崇拜的仪式。我们充满敬畏地观看,然后期待救赎。